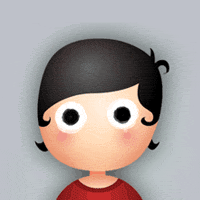在艺术史上,伦勃朗已被视为荷兰十七世纪黄金时期最重要的艺术大师。与三十年时期(1618-1648)的欧洲其他地区相比,荷兰社会处于相对和平之中,虽然参战,但未受战火严重波及,甚至击败西班牙舰队,一跃成为欧洲的新海权国家。在国家相对稳定的状态下,社会氛围亦显宽容。后,新教宗派纷立,荷兰改宗加尔文派,。在图象问题上,亦未坚持打破偶像,弃绝图象。许多新教教堂虽未悬挂图象,但创作图象的艺术家仍可找到新的买主。这种环境,成了伦勃朗创作大量图象的沃土。他的图象丰富多元,亦能坦然剖析自己的信仰。在以马忤斯(Emmaus)这个见证复活的故事中,伦勃朗亦着力甚深。
在的图象学中,以马忤斯的故事,大致分成三种表现方式,一是在道路上的相遇与陪同,一是邀请,最后便是戏剧性的擘饼与认出。在路上时,往往被画成一名戴着帽子的朝圣者,一方面以此解释门徒无法认出他的原因,一方面也反映了自西方中古以来的朝圣传统。晚餐的场面,则是这个主题较为偏爱的表现方式。文艺复兴之后,多半是与两位门徒围桌而坐,在中间,门徒各有不同显示讶异的动作,此外,画面一般多会再安排侍餐的店主或小厮或厨女,甚至会以静物画的方式呈现桌上的餐点摆设。不过,在谈伦勃朗的图象解经之前,我们先看看以马忤斯中的神的作为与神学关注,或许可以更多体会伦勃朗的诠释角度。
伦勃朗(手稿)
在最后晚餐之际,说出:「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回答门徒多马的问题,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因此,也不知道会走上哪条路?使徒约翰大篇幅地记录下在最后晚餐中的话语,也点出门徒当时的困惑与不安,到了隔天受难后,这种困惑与不安益形强烈。然而,一如的承诺,,但他会再来见他们,让他们喜乐。果然,在受难三天后,这件事如实发生。
在离耶路撒冷约二十五里的以马忤斯路上,以行动响应了门徒,他来到两位门徒身旁,陪他们走了一段路,最后让他们知道他复活回来了。在复活的那天,先是几个妇女在的坟前遇见天使,要她们不要在死人中找活人,因为「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这个信息让门徒们惊讶,也很快传了开来。当时,有两名门徒正往以马忤斯走去,看来一路上都在谈论这件奇事。
梅洛(1491–1543),《以马忤斯路上》,1516-1517,木板油彩,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
这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在画面中,将画成一位朝圣者,戴着饰有海贝,象征朝圣着的大盘帽,手拿一根杖,从后面赶上来问候门徒。远处类似城堡的城镇,便是以马忤斯,可以见到将到城门口的与门徒一行三人。画家梅洛在这运用中古常见、在同一个画面中讲述不同故事与场景的叙事手法。两位门徒对这位陌生的路人说了在耶路撒冷受难的事,因为看来整座城市都对此议论纷纷,这位陌生人不该不知道。他们也提到他们中间的几个妇女传说已经活了的事,但他们自己只是感到讶异,对这个复活的传闻不置可否。对门徒的这种反应,看来有些失望,一开口便说他们是无知的人,说他们的心信得太迟顿,然后将中指着他的话一一对他们讲明。两位门徒听着,心里感到火热,之前的愁烦难过一扫而空,原本的盼望似乎再次被挑起。
杜乔《以马忤斯路上》,1308-1311,蛋彩木板画,意大利西耶纳大教堂博物馆
意大利中古时期的画家杜乔笔下的,一样也是一位朝圣者,一样有一顶帽子和手杖,他的衣服让人想起施洗者约翰在他之前出来传讲天国信息时的穿着:「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两位门徒期待地看着,其中一位做出邀请进城的手势。
《以马忤斯》,出自:1748年荷兰文国会
这张铜版画把邀请的场景挪到客栈门口,鲜明的光线对比,点出了邀请的时刻,拄着手杖,左手指着前方,准备继续前行的样子。
提香《以马忤斯的晚餐》,约1535,油彩画布,卢浮宫
提香的晚餐画面,尤其是左边的那名门徒,姿态样貌都像《最后晚餐》中的犹大。在画面中已经擘开面包,门徒认出了他们的老师,左边的感到惊讶,右边的开始祝祷。餐桌的摆设安排,十分细腻,衬底的东方地毯,宛如丝绸的白色桌布,桌上的面包、醒酒瓶、酒杯、盐盅、水果,甚至一些散落的丁香花瓣,以及餐桌下的猫狗,在在显示提香这张作品在故事之外的许多考察,多少需要迎合委托作画者的身份与地位。
这个的信仰与信仰经历,在伦勃朗一生中,烙印下深刻的痕迹。他是画家,以画笔书写,甚至可以传达出他和信仰的互动,也反映出他每个生命时期的信仰内容。在十七世纪的荷兰,信仰告白是个棘手的问题。伦勃朗的父亲是后的新教徒,,而他五个孩子,都是在新教教堂受洗。他的画作,题材相当丰富,。二十岁出头,伦勃朗展开了他的职业画家生涯,那是一段自信与绽放才华的时期。二十八岁时,他娶了大画商侄女萨丝琪雅,生命对他来说,似乎已臻圆满。这种年轻气盛的特质,自然反映在他的创作上。1628或1629年创作的《以马忤斯的晚餐》,便是一个代表。
伦勃朗《以马忤斯的晚餐》,1628-1629,油彩画纸,39×42 cm,巴黎贾克玛‧安得烈美术馆
这个主题传统的表现方式,皆是居中,两位门徒分居左右。伦勃朗则一反这个构图方式,采用对角线构图,将置于画面右侧,在擘面包之际,身体后倾。他的光线运用,亦是追求强烈对比,光源看来不是墙面下方的某个微弱的烛光,而是接近现代的大瓦数灯泡。在这种光线下,几乎成了剪影,无法辨识出他的容貌。这个时刻应是正要消失的那一刹那。一名门徒惊讶地侧过身子,像是在躲避,他的上方,挂着他的行囊。桌面上,摆着一些简单的餐具和他们正享用的食物。如果不仔细留意的话,基本上会忽略掉那位在黑影中跪下来的门徒。画面左半部,一名厨女在远处同样以烛光中的剪影方式呈现出来,身子向前弯倾,与的身子近乎平行。
透过这个画面近乎四分之三被黑暗笼罩的作品,伦勃朗想要表达什么?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赋予明暗对比法新的戏剧张力,影响一整个世代的画家,奠下巴洛克艺术的基础。伦勃朗虽未出国前往意大利,也未见过卡拉瓦乔的作品,但透过其他画家的作品认识了明暗对比法,亦赋予了明暗对比法另一种高度。在这件《以马忤斯的晚餐》的作品中,伦勃朗看来浸淫在雕塑光线的乐趣中,厨女那头微弱的光线,似乎迷失在浓郁的黑暗中,迂回地与剪影后的强烈光芒呼应。画面中的强烈明暗对比,为添上了些许神秘的意味,不由得让人想到约翰福音中的经句:「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在伦勃朗看来,是种崇高神圣的,善恶泾渭分明。在他之后几年的作品中,这种荣耀圣洁的光线似乎遗世独立,绝不沾染黑暗。1634年,他的《卸下十字架》,再次让我们看见这种戏剧性的烛光。画面中,攀爬在十字架旁梯子上的一名男孩,以帽子遮着烛火,照亮了瘫软的身躯。生命与死亡的对比,在的身子与画面其他的人物中,显得刺眼。这是一个失去盼望的时刻,一个死亡掌权的时刻。然而,三天后,情势彻底翻转过来。的复活,成了信仰的基石。
伦勃朗 《卸下十字架》,1634,油彩画布,158 x 117 cm,圣彼得堡隐士庐博物馆
1626年起,伦勃朗开始创作蚀刻版画,而其成就,不仅与其绘画等量齐观,也睥睨当时的版画艺术家。同样,他也透过蚀刻创作了他偏爱的主题。1634年,他创作了一幅《在以马忤斯的》蚀刻画,虽然戏剧性不像他之前那张油画作品强烈,但是光线依然丰沛。整个光源来自画面右前方以及自己的圣光,不过这次,光线布满四分之三的画面,让我们看到更多的细节。
伦勃朗《在以马忤斯的》,1634,蚀刻版画,10.2 x 7.3 cm。
伦勃朗《以马忤斯的晚餐》,1648,油彩木板,68×65 cm,巴黎卢浮宫
在上面这一幅1648年的《以马忤斯的晚餐》这张作品特别之处,仍是伦勃朗擅长的光影。画面的空间显得高大,画面重心略往左移,为了刻意留出右边的门洞,那是个黑暗的角落。光源来自左上方的户外光线,温柔地弥漫在空间中,洒在白桌巾上,并流窜在许多角落。光与暗在这张画作中,不再是截然的对立,而是一种和谐的互动。和之前同主题的画作相比,这种改变是相当明显的,这不仅只是画作结构的改变,也是画家心境的改变。1642年,伦勃朗的妻子过世,成了他生命的分水岭,经济状况开始恶化。他搬离阿姆斯特丹,来到乡间。这个改变,让他开始着墨风景,对自然光线有了新的认识,生命也从年轻的狂放,开始有了新的感悟,画作也因而圆柔内敛起来。这时他笔下的,犹如日常中的恩典,随时顾念着他的孩子,一如画面中那温柔流淌的光线。
伦勃朗《的消失》,约1648-49,笔墨素描,20×18 cm,英国剑桥费兹威廉美术馆
在伦勃朗的生命中,以马忤斯的遇见,是他不时挂念的主题。从他留下的素描作品中,可以揣测他企图多方诠释这个主题。例如,他在1648-49年的一张笔墨素描中,描绘消失的场景。这种超自然的场面,在传统的教图象中,未被重视,主角缺席的表现方式,近乎叛逆。毕竟,素描作品一般多是艺术家创作概念的实验工具,而非可与观众一起分享的正规之作。或许,这是伦勃朗的一种尝试,想要打破传统常规,但在思索之后,并未落实。
伦勃朗《在以马忤斯的》,蚀刻版画,1654,21 x 16 cm
伦勃朗放弃了《的消失》的大胆表现方式后,反在古典的规矩中,找到新的灵感。1654年的《在以马忤斯的》的蚀刻版画,的姿势,让人想到达芬奇的《最后晚餐》,而的容貌则多了威严。
伦勃朗《以马忤斯的晚餐》,1660
来源:时报
声明:感谢作者辛苦付出与创作,版权归属原作者,如有版权问题欢迎留言联系删除。
以下经典好文,你可能会喜欢,点击蓝色字体即可进入文章:
史上最好笑,道理最深刻的文章
千万不要相信”人性“!(深度好文)
远离你身边的中国式“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