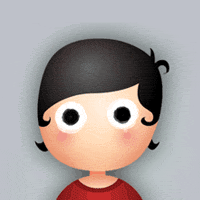编者按:
5月30日,之前被传死于谋杀的俄罗斯记者巴布琴科出现在一场高级别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情报部门的确打算将巴布琴科“消灭”。为完成这一计划,俄罗斯人已经策划了两个月的时间。乌克兰国安局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刻启动对巴布琴科的保护行动。,散布记者巴勃琴科被害的消息是特别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防止他被谋杀。
巴布琴科曾在1990至2000年代初期,担当俄罗斯士兵到车臣战争前线作战。成为记者后,他尖锐抨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工作。
本文原题为《不一样的“战壕真实”:巴布琴科的战争小说》,作者胡学星,原载《读书》2017年1期。
巴布琴科
阿尔卡季·巴布琴科(一九七七— )是第一位以车臣战争为创作素材的俄罗斯作家,他以充满人文情怀的笔法,将自己亲历的战壕生活展现给读者,其创作风格让人一下子就联想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壕真实派”。在苏联时期的战争文学领域,继老一辈作家法捷耶夫、肖洛霍夫、西蒙诺夫之后,出现了“战壕真实派”。该派作家大多是在前线打过仗的年轻军官,他们结合自己在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创作出一批堪称经典的战争文学作品,包括邦达列夫的《最后的炮轰》、巴克兰诺夫的《一寸土》、贝科夫的《第三颗信号弹》等。“战壕真实派”的创作出发点有别于此前的苏联战争文学,没有将战争的胜利全部归功于最高统帅的英明指挥,而是将镜头对准了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普通官兵,突出了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无可替代的贡献。相对于此,车臣战争作为一场现代局部战争,缺少那种全民皆兵、同仇敌忾的高昂情绪,战争似乎与普通百姓无关,而参战士兵也将前线作战理解为一项职业任务,很少表现出英雄主义气概或爱国主义热情。因此,巴布琴科的车臣战争小说虽然同样力求表现“战壕真实”,但他笔下呈现出来的战争已是另一种样子。
车臣战争
巴布琴科创作的初衷首先在于揭示车臣战争的真相,对“战壕真实”的再现达到了新闻报道那样的准确程度。在谈到文学创作时,他宣称自己的作品反映的就是“战壕真实”,要将“亲眼看到的那种战争呈现出来,不会是那种被宣传加工过的样子”(二〇〇八年四月七日接受BBC采访)。评论家普斯特瓦娅曾撰文,专门谈到了巴布琴科小说的这种真实感:“巴布琴科被战争的真实压得喘不过气来。像一面镜子的碎片,穿行在战场上,并将战场映射出来。”(《新世界》二〇〇五年第五期)为了强调这种“战壕真实”的价值意义,巴布琴科曾与老一辈作家马卡宁(一九三七— )展开论战。马卡宁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文学创作,数十年来笔耕不辍,代表作品有《铺着呢子,中间放着长颈瓶的桌子》(一九九三年获俄语布克文学奖)、《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一九九八)等。一九九九年,马卡宁推出了以车臣战争为背景的中篇小说《高加索俘虏》。在马卡宁看来,即便是对于战场上经受生死考验的人,美仍然是一种拯救力量,它可以让人保持自己的本性。巴布琴科则认为这种论调纯属无稽之谈,为此他不无针对地指出:“没有打过仗的人不能讲述战争,这不是说他笨或迟钝,而是因为他没有能用来理解战争的感官。这和男人不能怀孕、生孩子是一个道理。”(《战争艺术》二〇〇六年第一期)二〇〇八年,马卡宁以车臣战争为题材,创作出长篇小说《阿桑》,并获得了当年的文学巨著奖。《阿桑》中的主人公建筑工程师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齐林,曾在车臣地区从事军火库和燃料仓库的建筑工作,在车臣战争之后成为俄军敬仰的汽油大王、车臣人敬畏的“阿桑”。就马卡宁的这部新作,巴布琴科在《新报》上做了毫不客气的批评,认为马卡宁对战争的描写纯属杜撰,根本沒有真实性可言,称这部小说是“借车臣题材对战争的胡编乱造”(《新报》,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八日)。在巴布琴科的小说中,饥寒交迫、惊恐不安才是士兵每天面对的生存状态,危机四伏的环境要求战士们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而美的东西背后往往暗藏着危险:“是很好,好看。但那儿会有车独分子藏身。那儿会有一场战斗,死神就在那儿。狗东西,潜伏在那儿,躲在太阳底下。等待,在等着我们。等我们懈怠了,就会跳出来。”(《阿尔罕-尤尔特》)
巴布琴科在小说中体现的“战壕真实”,摆脱了正义战胜邪恶、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等宏大叙事的诱惑,“活命”被视作战场上的最高法则。战争怎样让一个人变成一名战士,这才是他要表现和思考的主题。从生命价值的角度,巴布琴科将战场上的“活命”与社会生活中的“生存”等量齐观,战区类似于现实生活中的另一个街区,在战区里生活着一种从事特殊职业的群体。二〇〇五年在接受《新报》采访时,巴布琴科说过:“有两个俄罗斯,正在打仗的俄罗斯和另一个俄罗斯,它们存在于平行的两个世界。”在小说《阿尔罕-尤尔特》(《新世界》二〇〇二年第二期)中,通过主人公阿尔乔姆,巴布琴科讲出了战区“居民”最关心的事—“在极端情况下,所有机体活动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活命。”在生死瞬间,阿尔乔姆处于极度惊恐之中,他最为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活命”:“重要的是活下来。什么都不要想。至于将来会怎样,只有上帝知道。”阿尔乔姆将打仗等同于职业行为,杀人不过是这种职业要求完成的任务而已:“对车独分子,他没有丝毫同情或良心不安。我们是敌人。应该杀死他们,就该这样。采取一切手段。办起来速度越快、手法越简单越好。”我们还记得,在当年的“战壕真实派”作品中,颂扬英雄主义,捍卫正义与真理,是巴克兰诺夫等一代作家始终坚持的创作宗旨。无论是在《最后的炮轰》,还是在《一寸土》中,尽管战士们英勇战斗的画面充满了血腥,,成为捍卫和平与真理的高尚之人。在《一寸土》中,巴克兰诺夫借中尉莫托维洛夫之口,道出了苏联官兵为赢得战争胜利而忘我战斗的意义:“我们打仗,是为了消灭所有的卑鄙行径,是为了战后能过上充满人性、诚实而正当的生活。”不难看出,在“战壕真实派”的作品中,消灭敌人而让自己活下来并不是最终目的,这显然与巴布琴科的“战壕真实”所体现的“活命”原则不能同日而语。
在巴布琴科的战争小说中,作者从全新的角度开启了当代人对生命的意义、对战争的另一种理解。参与战争的人遵循着冷酷而僵硬的“活命”原则,由一个普通人变成一名战士,完成这种蜕变的代价是人性的丧失,这与战士对和平生活的渴望产生了难以克服的冲突。在现代化战争条件下,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交战双方或阵地已不复存在,交战经常发生在人们仍在正常生活的街区或巷道,执行作战任务的战士穿行在和平生活的空间之中。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对和平生活的渴望就变得格外强烈。此外,现实中车臣战争引起的社会关注度不高,新闻媒体对战事没有连篇累牍的报道,退伍后的战士也感受不到社会的关心,体验不到参战本应带来的自豪感,由此产生的落差让参战者更看重普通人所过的安宁生活。巴布琴科在描写令人胆战心寒、噩梦萦绕的战斗场景之际,始终未忘展示主人公内心对正常生活的向往与渴望。战争残酷之“冷”与向往和平生活之“热”交织在一起,在这种冲突中,主人公一方面要捍卫“职业”操守,去完成作为战士所肩负的任务,另一方面还要像普通人那样,时刻想着保全自己的性命。为此,巴布琴科所要表现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和敌人的冲突,而是主人公内心的冲突。小说中塑造的主人公不关心为什么而战,为谁而战,战争对他们来说更像是必须完成的工作。在巴布琴科的作品中,普通人经受战争的考验,成为一名战士,这并不意味着他在人格上的升华,也不能证明他在价值观或人生观方面变得更崇高。相反,人之蜕变为战士,往往意味着心灵活动的结束:“这片战场他不会忘记,他是在这儿死去的,他身体里的人跟在纳兹兰时的希望一起消逝了。而一个战士诞生了。一个好战士—空虚、没有思想,带着冰冷、仇恨的心看待整个世界。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阿尔罕-尤尔特》)
在巴布琴科的小说中,按“活命”原则,将个人的生存放在首位。阿尔乔姆是小说《阿尔罕-尤尔特》中的主人公,在一次执行任务时,由于他的误判,导致一名车臣老人及其八岁的孙女遭到枪击,女孩当场死亡。这件事让阿尔乔姆追悔莫及,几近疯狂,差点儿吞枪自尽。为了证明“活命”的合理性,他反过来想,被枪击的目标如果真是车臣匪徒呢,那样的话,命运就换过来了,死的就不是对方,而是自己了。最后,阿尔乔姆认识到,开枪是必需的,由此也完成了由普通人到一名战士的蜕变。在这个蜕变过程中,将个人放在首位的“活命”原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与以往的战争文学大相径庭。人们在谈论“战壕真实派”的起源时,常常追溯到维克多·涅克拉索夫(一九一一至一九八七)的中篇小说《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一九四六)。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克尔任采夫中尉在前线的所见所闻及其成长过程。在反击德军的战斗中,人之成为战士,意味着这个人经受住了考验,其人性得到了升华,进而变成英雄。对于涅克拉索夫来说,战争是验证和提升人格境界的手段。对于巴布琴科而言,战争中的人也是普通人,而战区不过是另一种生存区域而已,争取活下来才是天经地义的头等大事,这成为其作品中缺少英雄人物形象的原因之一。
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将主人公“平民化”是巴布琴科战争小说的一大亮点,这有别于以往带有“英雄化”“妖魔化”倾向的做法。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壕真实派”文学中,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大多表现出主人公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存在着英雄化的倾向。在八九十年代关于阿富汗战争的作品中,不仅见不到对英雄主义的颂扬,而且表现出另一种极端,即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存在着“妖魔化”倾向。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奥列格·叶尔马科夫(一九六一— )曾在苏联驻阿富汗的炮兵部队服役。一九八九年,叶尔马科夫开始根据亲身经历,创作出系列小说《阿富汗故事》。在叶尔马科夫的代表作《野兽的标记》(原文发表于一九九三年,由刘宪平、王加兴完成的中文译本已于二〇一五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主人公切列帕哈是苏军的一名校炮手,小说重点讲述的不是他在战场上的表现,而是其所在的军营生活。借助“妖魔化”手法,切列帕哈被塑造成一个与“野兽”无异的军人形象,他不仅欺负新兵,吸食,还恫吓平民,枪杀俘虏。而在阅读巴布琴科的《山地步兵旅》(中文译本见《世界文学》二〇一〇年第三期,胡学星译)等小说时,我们能从主人公平淡无奇的言谈举止中,深切感受到他们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珍惜,这都要归功于作者将主人公“平民化”的处理方法。
在巴布琴科的小说中,军人没有被塑造成“高大上”或“高大全”的形象,不過,他们还是会让自己适应残酷的战场生活,以尽职尽责的敬业态度,去履行军人的天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战士们在险象环生的战争环境中,每时每刻都在寻找机会体验和平生活,有时候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山地步兵旅》讲述了俄罗斯士兵与车独分子作战的种种经历,同时还不吝笔墨,描写了战士们在战斗间隙或休整期间的“闲情逸致”—到河里洗澡,收养小狗,救护濒死奶牛等故事。有一次,战斗刚告一段落,两名战士去车独分子把守的楼内侦察,发现“一个很像样的炉子”,便想带回去取暖用,这时候被对方的狙击手发现:“我们朝己方的楼房飞奔,像高鼻羚羊那样,两跳就跨过了五十米的距离,但还是没扔下炉子。我俩刚跑进楼门,就开始像疯子似的哈哈大笑,差不多笑了半个小时,停不下来。”为了弄到取暖用的炉子,两名战士差点儿丢掉自己的性命。这是正常人所难以理解的,因为人们不了解战士们所过的那种非人生活:“一个星期没洗的双手布满裂纹,经常出血,因为寒冷而变成了密密麻麻的湿疹。我们不再洗脸,不再刷牙,也不再刮胡子。我们已经一星期没烤过火了—湿漉漉的芦苇点不着,而在草原上又没有地方可弄到劈柴。我们开始变得像野兽一样。寒冷、潮湿和泥泞把我们身上所有的感觉都剥蚀掉了,只剩下仇恨,我们仇视这世上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正是为了避免变成“野兽”,需要用炉子来取暖,让自己保持正常人的状态,两名战士才会冒着生命危险将炉子带回去。
在巴布琴科讲述的车臣战争中,类似的故事并不少见。短篇小说《一套住房》讲的是俄军士兵入住攻占区无人留守的民宅时发生的故事。主人公发现一处住宅的房门上挂着钥匙,室内陈设简朴但很温馨:“在一号小区,在一座黄色的五层高的楼里,我发现了这套住房。房门上包饰着便宜的人造革,门锁上插着一串钥匙,主人没打算把门锁上:在这里住吧,别破门而入就行。房子并不豪华,但很齐全。很有生活气息,看来主人刚刚离开,就在突袭之前。不像是在战争时期,这里很温馨、安静。简陋的家具、书籍、陈旧的壁纸、毛织无绒头的双面地毯。所有东西都收拾得规规矩矩,没有遭到洗劫。甚至连玻璃都没被打碎。”房子的主人非但没有将家中的物品带走,还把钥匙也留了下来,这让见惯了人去楼空的主人公产生好感,唤起了他对和平生活的渴望。于是,他将这一处住宅“藏匿”起来,经常到此待一会儿,将房主想象成自己的妻子,与之一起享受片刻的安宁生活:“这里是一个小世界,是我极其渴望的安宁生活的一片小天地,我渴望从前没有战争时的那种安宁生活,可以和家人在一起,守着心爱的妻子,晚饭时边吃边谈,畅想着未来。”在故事的结尾,主人公再次来到那处由于他的努力而保持完好的住宅:“我们要继续向前开拔时,我最后一次去那儿看了一眼,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仔细地把门锁上。我把钥匙留在了锁上。”
从这类故事中,我们看不到战士们追求建功立业的英雄主义,也看不到那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然也无从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作者对战士的污蔑或贬损。换言之,巴布琴科的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既不热衷于“英雄化”,也不喜欢“妖魔化”。巴布琴科描写的战士活跃在战场之上,辗转于生死之间,但仍渴望能像和平环境中的人们那样过正常生活,做个正常人。可见,“平民化”才是巴布琴科塑造军人形象的手段,这让他笔下的战士更真实,更接地气。
在巴布琴科尝试战争文学创作之时,苏联解体后一度受追捧的后现代主义已风光不再,现实主义传统开始回归。在这种文学背景下,巴布琴科追求“战壕真实”的小说一经问世,便被评论家贴上了“新现实主义”的标签,并得到涅姆佐尔、斯拉夫尼科娃等文坛大腕的一致力捧。近年来,巴布琴科受聘为《新报》等媒体的战地记者,多次到南奥塞梯、乌克兰前线采访,这无疑会为他今后的战争文学创作提供帮助,我们期待着他更多更优秀的作品问世。